
《长篇小说卷》导言
阎欣宁
如果说一位小说家的成熟,在于熟练地驾驭长篇小说的技巧——而非简单地出版长篇小说的话,那么,一个地域性的小说家群体的成熟标志,或许在于其长篇小说的团体状态是否老到成熟,所谓团体状态,正是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的编选成书已进入第三轮了,十年一个周期,恰好是“三十而立”的黄金岁月。年届三十,难道不该而立而有所作为吗?
经再三筛选,我们择取了十八部长篇小说的节选,作为这一团体状态的成果汇报。
十八部长篇小说呈现出来的姿态各有千秋,正如十八般武艺的逐一展示。十八位作者的谋生饭碗各有不同,他们中既有政府公务员,也有新闻记者、文学编辑和文化从业者,还有甘愿扔掉铁饭碗从事专业写作的“自由撰稿人”,五花八门,多彩缤纷。就年龄来看,从“五O后”到“八O后”,其中甚至囊括了母子二人,可谓真正地跨越了两代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多少年?“十八”是个接近于无限可能的大数,是步入成年的标志,更隐含着各种担当的意味。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沙家浜芦苇荡里的新四军伤病员,都是“十八勇士”。当然,活跃在当今文坛的厦门长篇小说作者远不止十八位。他们在头悬低稿酬、高额税这把利剑的过往十年中,视温饱为满足,耐寂寞为清雅,伏首电脑鬼火般的荧荧光影下,十指叩击着心灵,心血泣诉着人生,奉献出的远不止十八部作品。十年来,恐怕还包括将来,业余小说作者之难,不在于写稿,而在于出书。即便是出版渠道,亦是八仙过海一般,各有神通,或端庄傲气,或忍声吞气,甚至“割肉附血”地迫以自费……长篇小说出版难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十八部长篇小说的文学成色。朱门酒肉浸大的是孩子,茅屋稀粥喂大的也是孩子。但凡舞文弄墨者,心劲、心气都不小,人人心中一处圣境,人人皆是自己的上帝,丧失了自我便丧失了自己的文学天地。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素养,各自取道不同的文学走向,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中,十八位作者各有一番拳脚。
曾获得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的《天堂没有路标》,其写作难度在于以小说反映近代名人林巧稚,但凡人和事皆真,作为小说就落笔两难了。实,还是虚?虚构的空间一旦受到局限,小说家犹如踏在扁担上起舞。赖妙宽较好地破解了这个难题,大胆的文学尝试获得了业内认可。过去的十年,厦门的儿童文学创作犹如羞答答的玫瑰,悄然绽放,其光彩夺目却令那诸般妃紫嫣红猛吃一惊,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堪称“厦门双妹”的晓铃叮当和李秋晁。前者凭借《魔法小仙子》夺得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后者在数度拿下“冰心文学奖”之后,其《木棉·流年》又一举斩获了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女汉子”们不让须眉,袁雅琴的《堕落街》、丽晴的《南下干部》、张宇的《妖烧无边》,都在各自熟识的前庭后院创坑栽树,赏那根深与叶茂。而扎扎实实的一批“中坚男”,则以务实的勤恳,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苦耕不辍。嗜茶如命的夏炜,以《铁观音》为茶乡、茶话做了一部“史”;新闻媒体人王海青以自己难得的闯南极经历,奉献出了《南极考察队》;执着于乡土文化的曾纪鑫,以《风流的驼哥》为自己留下了一段故乡记忆;以真实为操守的新闻人高渔,却在《魔术师传奇》中尽现了艺术想象的神幻功力;同为新闻人的江俊涛,在《安居》中却以写实再写实的手法描绘了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刘岸的新疆边关情结在《尘土飞扬》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宣泄;海关作家金小刀,在《困局》中则娓娓诉说着一个远不止是行业内情的故事;有着特殊经历的吴尔芬,则在《九号房》中讲述着一个中国式的“楚门的世界”的故事……此外,韩韵的《剩女单身日记》、森泉的《走过水木年华》、赖建宏的《我们的爱情无处安放》、花舞陌轩的《倒带》和高鸽的《越魂》,则从书名甚至笔名中揭示了文学的另一走向:更为宽泛的大众阅读取向,青春写作中新潮的语言叙述和文字张力,使他们在读者群中赢得了更多年轻男女的青睐,这也是此类文学作品更容易转向影视之途而获得更多传播渠道的原因之一。
长篇小说选本,以寥寥两万字左右的篇幅以期窥斑知豹,其局限性可想而知,正如你登上了日光岩或踏上了环岛路,便自认为探得了厦门的真韵,那都不是真的。能从一滴水里折射出太阳的万丈光芒,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我们所能做到的,或许仅仅是“索引”而已。
应当指出的是,固于篇幅及选报“规则”,更多“厦门制造”的长篇小说,甚至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都未能入选本书,例如须一瓜的《太阳黑子》等。这一遗珠之憾,只能说是我们与广大读者和作家的共同之憾了。
201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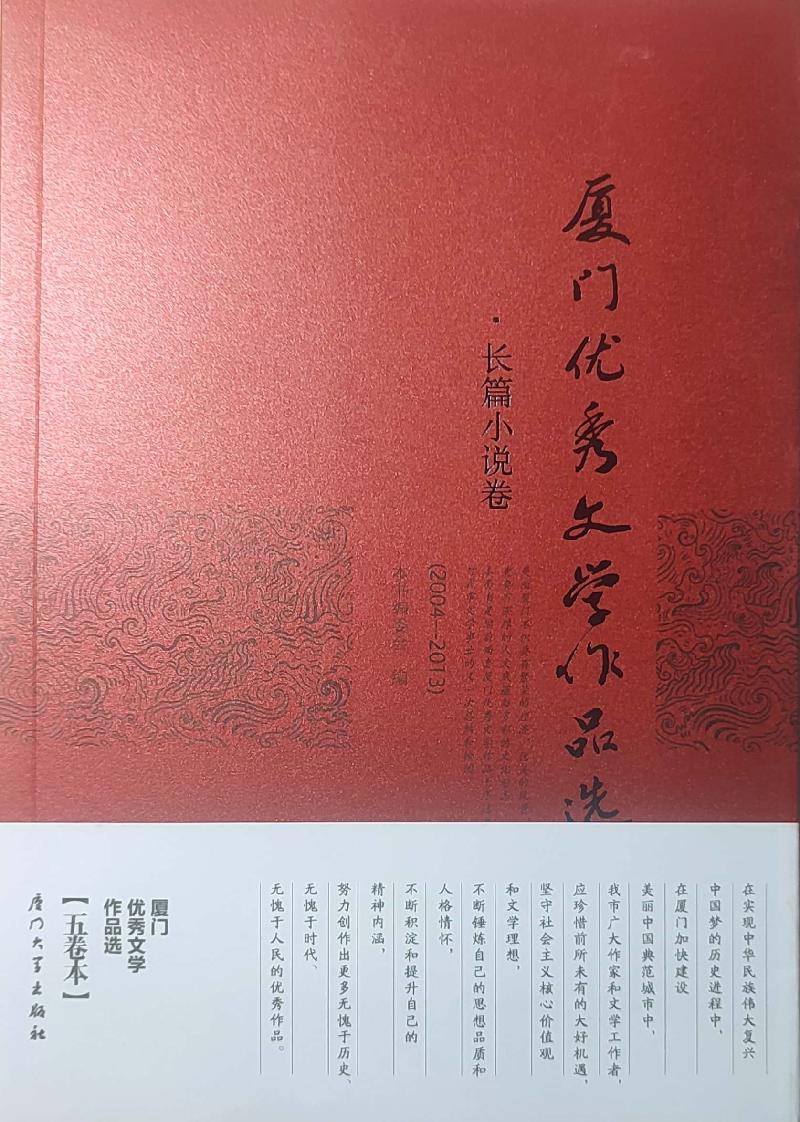 50.00
50.0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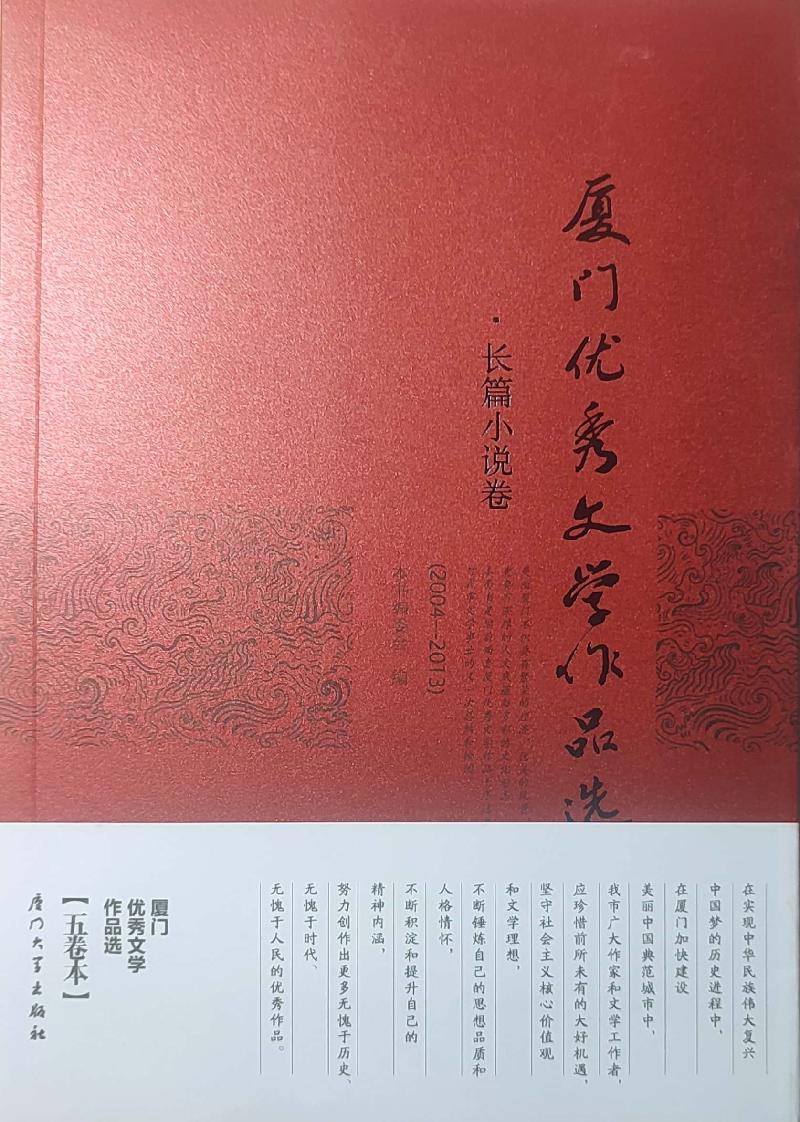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