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短篇小说卷》导言
(节选)
朱水涌
这是一部在人类欢度过千禧年之后中国一个海滨城市的小说结集,是厦门人走在21世纪开元后十年行程上的一个叙事选本,27篇中短篇小说,就像鹭江那延绵激荡的浪花,给了读者对于厦门文学一种美好的想象,一种叙事自信的艺术期待。十年一剑,从1993年开始,这已是第三个10年编选的厦门优秀文学作品,也是我第三次参与厦门优秀小说选本的编选与导言的撰写,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选本专门为长篇小说立卷,这表明厦门文学正在向更加厚重、更加开阔的表达领地掘进。如果说1993年以前十年的厦门小说喷发的是历史新时期火热的思想、生活的激情,1993年之后十年的厦门小说在多元叙事中有引人瞩目的实绩与惊奇,那么最近十年的厦门小说,更像那平静的海洋中的潜流,积蓄着叙事的力与量,向往着一次艺术的重新爆发。这不仅是因为选在这里的20多位作者有许多年轻的面孔,在文学极度边缘化而市场横行于世的今天,还有那么一群青年在执着地勾勒锻造人的灵魂,这是这座城市很让人欣慰的精神现象;而且这力与量,更体现在读者可以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沉潜,无论是在人们熟悉的作家笔下还是在那群刚刚步入文坛的新生代抒写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今天文学的沉稳与坚守。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小说并不像今天的小说那般沉静,那时小说基本延续与传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包含着对旧的批判与对新的呼喊,有人称其为青春激情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是以激烈地否定前人来确立自己的价值的,文学代时代的变革发言,文学以其先锋性调整着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培育新的时代精神。所以文学的发展形态是潮流更替媳变,大有“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十天”的架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文学的现状与发展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变动,不再是青春激情的写作,不再是以否定前者来确立自我的存在。时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市场经济的中心位置、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震荡,都意味着文学的呐喊会被更为理性的精神思考与现实审视所代替。文学被边缘化了,但这样的边缘化恰恰带来了文学的常态与沉稳,思潮的這变更替消失了,代际间的冲突争论淡化了,代之而起的文学,除了新媒介带来的文学新形态外,最重要的现象是文风进入了一个比较沉稳的发展时期,一种沉潜坚韧的理性思考与美学凝聚,给了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更富希望的憧憬。厦门最近十年的小说,大致也体现了这样的一种潜在。
那些沿着新时期文学发展路线图而走过来的作家,这种沉潜坚初的理性思考与美学凝聚会更为鲜明,须一瓜的中篇《智齿阻生》就是一个证明。须一瓜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中篇叙事艺术的代表,一位颜受当代文学界关注的厦门女作家,她那以机智精致的叙事追问人性的班驳复杂以及生命疑难的创作,时常会让评论家惊异于她的表现、她的构思和幽默的双关话语的波俏。“边界模糊,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脆弱与复杂,看到了人性真实”,这是这篇小说的叙事动机。
一位畏惧黑暗、日常保持洁净的普通检察官,遇上一包装有几十万元的大纸包,纸包来得恰是时候又自然巧妙,于是边界模糊的事物引出了检察官人生边界模糊的瞬间,纠结、挣扎、反反复复的内心较量,面对着外在的难以抵挡的诱惑,原本那么有定力的检察官陷入了仿徨与混乱。小说的内容看似是当下人们关注的反腐题材,但须一瓜将叙事超越现实题材的拘園而指向人性的思考,指向一个很少有人揭示的人性边界模糊的瞬间,这就是她的叙事别致与艺术坚守。短篇《风雨总在彩虹后》是须一瓜对短篇结构的一次创意,它以当下流行的博文为基础,在一位成长少年的真诚目光与书写中展示少年日常生活的万花筒,有反讽,有荒诞,也有少年的向往,须一瓜总会在日常与平淡中观察到那些能赋予艺术意味的有趣细节。《婴粟花山谷》是一部值得深入阅读的中篇,作者刘岸是一位老道的小说作者,像“山谷的傍晚来临时,你听到了一个空洞而广衰的宇宙之音,它‘咪’的一声,月亮和星星就升起来了”这样的想象与描写,只有深谱文学特性与艺术语言的作家才写得出来。小说借一个漫游者的探寻,神奇地弥漫了23年前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罢粟花山庄所发生的一切正是远离文明时空的岁月存在。多重叙事者的讲述,后设叙事的应用,茂密的罢粟与大火遗留的灰烬,漂纱而来又漂纱而去的人物,还有那有意淡化的时间,都让人想到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小说叙事革命,想到马原、余华、格非,想到莫言,想到《百年孤独》对于中国文坛的影响。赖妙宽也是厦门的知名作家,她的创作总会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动发生些许的转变,与上一个十年写南方小城的芸芸众生相不同,这里的《仿佛硬汉》写的是一个与死神打了个照面的企业领导,这个决心要混出人模狗样的“硬汉”,前半生将性作为政治生命的大敌,却不料自己就栽在那上面;下半生他要与身上的肿瘤搏斗,这引发了他的不安、烦躁、委屈,在发现“手头所剩无几”的痛苦中,女人的存在成了他的“寄托与温暖”,然而他只是“仿佛的硬汉”,他已经很无奈了。赖妙宽将自己原本的世相描绘引向人性的开掘表现,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依然是她曾经表达过的生活无奈与生活怪圈问题。短篇《母亲的绿丝带》的作者是短篇小说的神枪手阎欣宁,这位曾经以“三枪”(《枪圣》《枪队》《枪族》)为军旅短篇打开局面的作家,其叙事结构的精妙和人物刻画的精准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近十年他的成就主要在长篇小说上,短篇《母亲的绿丝带》是他献给那些与汶川灾区人民血肉相连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的文字,这种传播正能量的创作很能考验一个作家的叙事能力。阎欣宁巧妙地以一条条绿丝带系到香炉上又从香炉摘下系到灾区小姑娘手腕上的平凡举动,将一位信佛的草民母亲为灾区人民捐赠的行为与地震中的儿子、好人和灾害的承受者联系起来,特别的视角与简洁的叙述让文本弥漫着人间的温情与生命的温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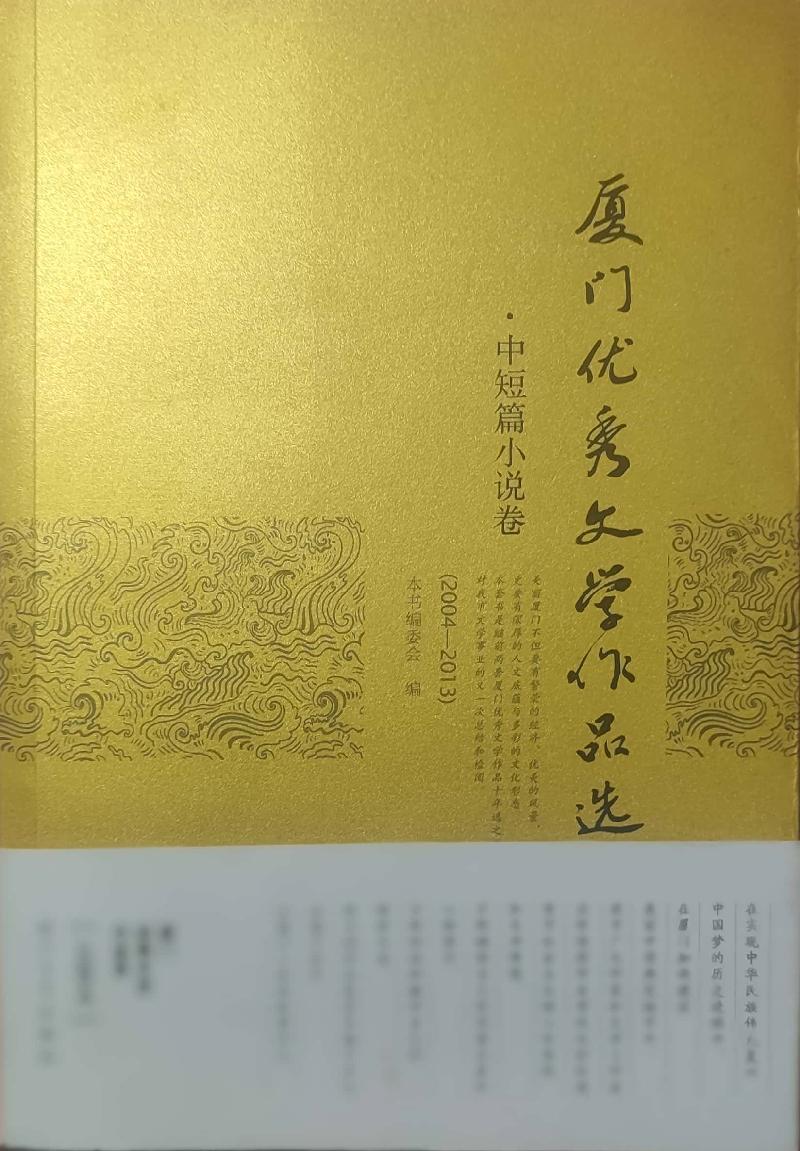 60.55
60.5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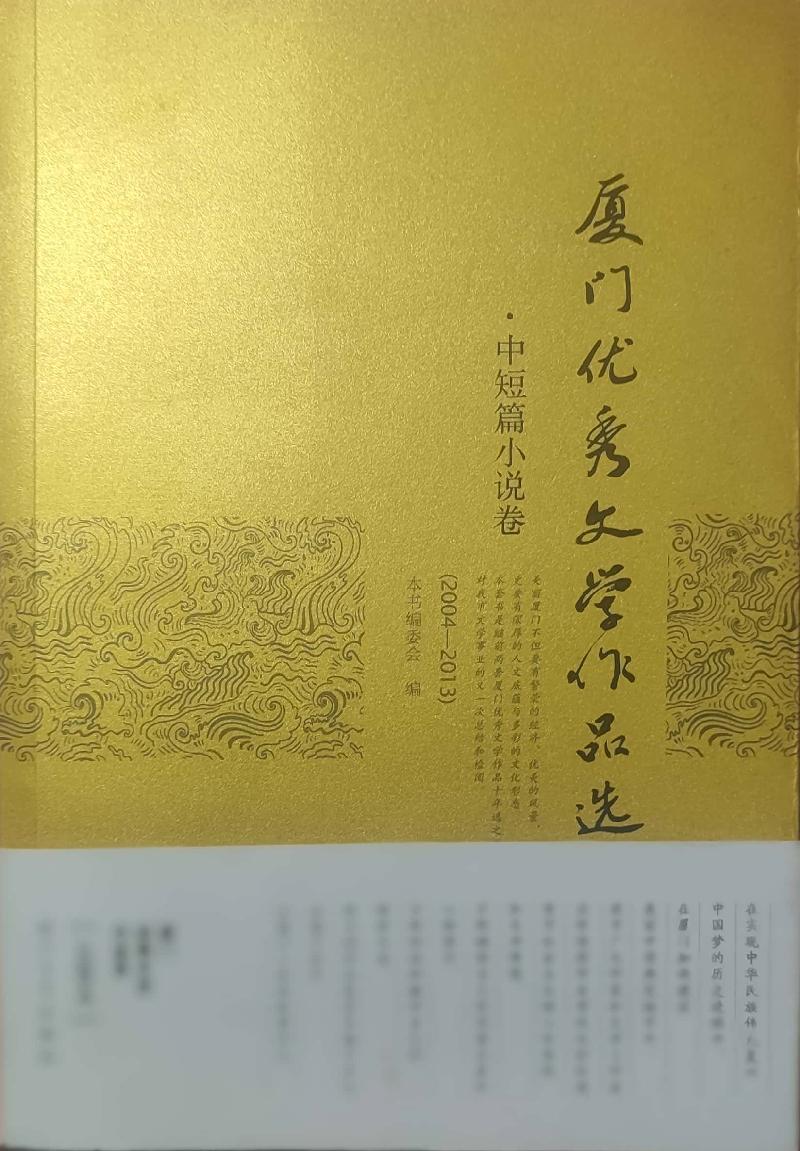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