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歌卷》导言
(节选)
陈仲义
一
这是厦门诗歌的第三个“十年”。
此前,20世纪80年代有过一段以厦门知青为主体创作群体的阶段,红红火火。90年代初期,情势陡然急转,剩余六七位本土诗人,艰难留守,相当寂寞。幸好,有特区改革开放大潮,吸引涌入大量“异乡人”,同时带来众多写作者与诗人加盟,厦门诗歌才有了转机。一切都在悄悄中孕育。不能忘记“第六晚诗歌沙龙”(重新睁开的复苏眸子)、“中国诗人网”(速成的模范诗写班),以及“顶点诗歌论坛”(日均帖300个)等的聚集与牵动,使得厦门诗歌的气候、土壤、氛围,开始有了新的格局。
毫无疑问,2003年是个重要“分水岭”— —
2003年,“厦门青年诗歌沙龙”第一次打出自己的“名号”,拥有了自己的纸刊《厦门诗歌报》。
2003年底,首届福建青年诗人交流会在厦门召开,“厦门青年诗人群”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2006年,《厦门青年诗人诗选》入选基本阵容57位,正步走出自己的方阵。
2007年《厦门文学》推山“厦门诗群”近200首诗作,提示了更多的潜质。
2005年创办的“陆诗歌”论坛,两年后推出同名纸媒诗刊,每期长达200多页,先后四期做专题性“扩招”—福建、台湾诗歌版图,早早超出了厦门地域。
《陆诗歌》创刊号曾宣称:“我们无意拉扯任何一面虎皮来自以为旗帜,无意凑热闹的观光者的兴致,而是给这个物质化的现实,留下一个诗人当下的线索和一点个人坚持的信仰。”这其实注脚了厦门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悄悄地,不事声张、自由而松散地写作、交流、生活,没有什么登高一呼的领袖型人物(如漳州诗群的陈道辉),也没有用全身心焚烧自己与诗歌的“烈女”(如北漂的安琪),更没有“事件”炒作、“运动”引爆,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是他们一个标示。如同2007年以来,他们平静而参差地推出个人作品研讨会12场次(非、子梵梅、南方、冰儿、威格、叶来、周莉、华晓春等),默默而扎实地构筑着他们优质的“诗生活”。
在诗歌界,人们喜欢用比较视域的眼光做一番“排行”。以笔者有限的感知做一下粗略判断,厦门诗歌无论是以“副省级”城市还是以“单列”或“二线”的名义参赛,其整体数量与质量当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主要依据是:近十年出现了近百名诗歌作者,出版了四五十部诗集,有几位诗人进入或正在进入全国性视野。
厦门诗歌的第二个“十年”,如果说,是以舒婷《最后的挽歌》作为自然谢幕——意味着舒婷的诗歌时代业已结束,那么,接下来是颜非们与子梵梅们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二
70 后出生的颜非外表腩腆、羞叔,吐露内心世界柔弱、宽怀的一面,但并不表明他就放弃与世界“古老敌意”的方式,这种方式竟是天性般退回到往昔、童年、记忆与伤疤之中。他所经营的一切“老旧”题材,都可以隐约寻绎到其生长原点、血缘与基因,使得创伤性缅怀,植入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并兼具现代“回味”。温厚怜悯的情怀,匹配很强的叙述能力。小说的基本元素在分行处理中完全溶解,或者说,在有限的分行排列中,他把小说元素进行精致的最大化。代表作《鱼,玄机》(获本省百花文艺奖),完全可与翟永明《鱼玄机赋》相提并论。其最大成功,是对历史、现实、时空的巧妙切换,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以男性少有的细腻阴柔克服了干硬泥实的通病,显示了四通八达的艺术“勾搭”能力。
笔者特别看好子梵梅《一个人的草木诗经》,这是将100种草木做成图文并茂(摄像、题记、注释、诗本)的跨文体,应该说是厦门乃至福建省诗歌近十年来的重要收获。她的灵思奇想,织就人生比附与人格“比德”的百锦图,在在把郭老的《百花齐放》远远甩在后面。笔者就此比较写出万字论文参加海峡两岸诗歌交流(《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近年来,子梵梅从过往繁复的隐秘中走了出来,试张小云和威格同属后现代消解性写作,小云通常在汉字符号的常规体操中,意外地抖出自选动作,让人忧然了悟现存规约的弊端,旨在冲击传统中庸思维习惯。威格一方面从流行的实用文体中,振动那些连排的朽木,探触背后的黑暗,另一方面,用童话、寓言,“壁虎般的冷笑”,反讽了“庞然大物”,有一种坚硬的“毒”。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周莉的《复仇女神》写得淋漓尽致,形式上介于诗与散文诗之间,一如她的副题“在深蓝与魔鬼之间,是我”。建议周莉在“像与不像”“似与不似”的夹缝中,继续走出自己的诗歌美学。此外,陈功对现象的思辨和由思辨导入的诗思尖刻、凝练而不乏穿透;同一写作维度的曾弗,持续开凿他的深度意象,冷峻而略带孤绝;对日常细小事物的抚摩,南方可谓行家里手,体现了女性特有的灵性感触与别致;叶来对生活的直接干预,集中于系列性的“县后路”素描,颇具“行吟戏拟”的况味;江浩的乡土深情,全部献给了“土楼”的长篇咏叹,他的风格与他的名字是如此对称……这一切,都充分展示了厦门诗歌各具特色的路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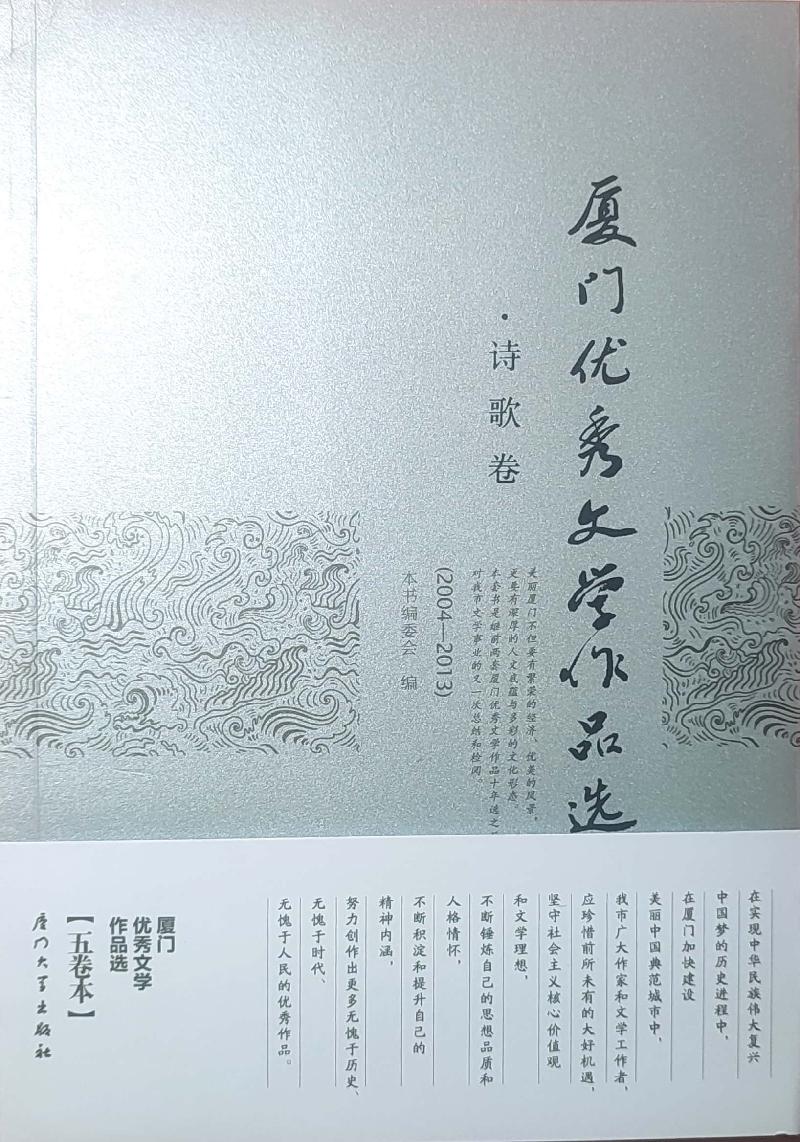 35.00
35.0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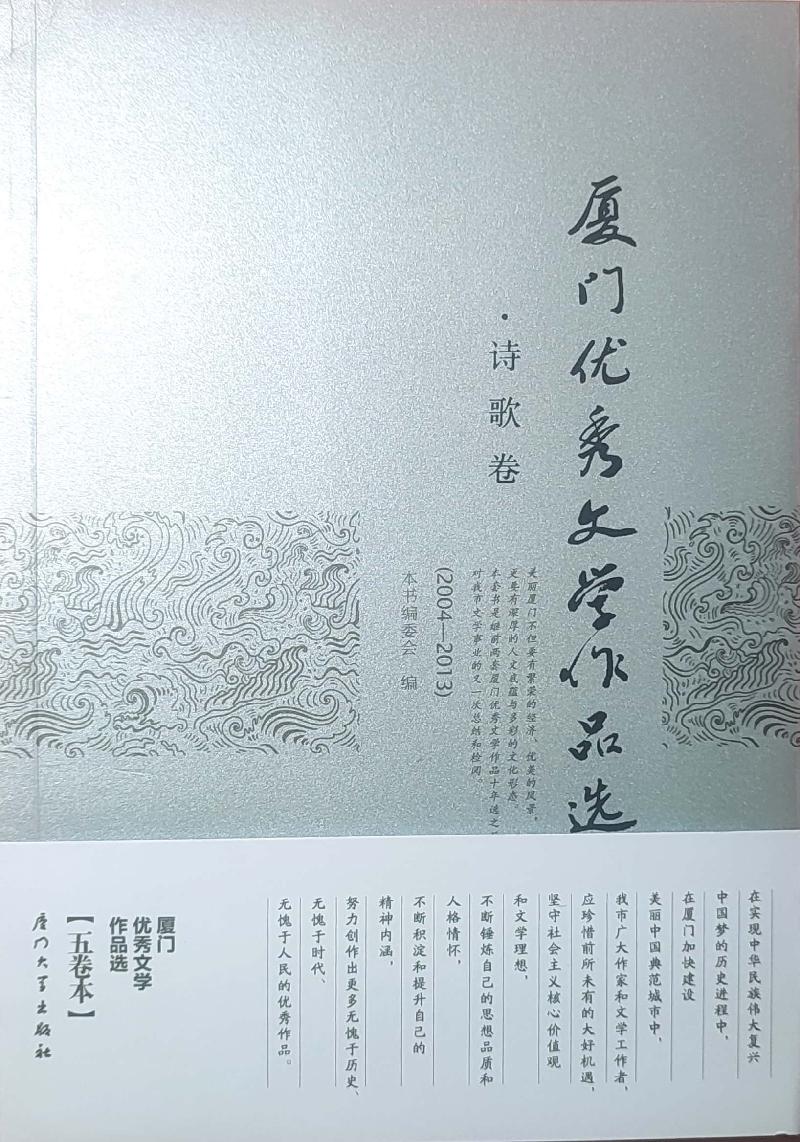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