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卷》导言
(节选)
何况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有个基本判断:“六经之中,除《诗经》外,全系散文;《易经》、《书经》与《春秋》,其间虽则也有韵语,但都系偶然的流露,不是作者的本意。从此可以知道,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韵文系情感满溢时之偶一发挥。”
我在微信上与文友讨论郁达夫的这一观点时,全国戏剧文华奖.
大型剧本奖得主汪水发先生表示赞同,他说:“当文字尚未发明或发明而未得到广泛使用的时候,文学早已产生。那时的文学只能是诗歌,利用语言的音韵节奏,便于记忆与传唱。文字来了,散文也就登场了,因为人不可能都如顺口溜那般讲话,而记录零散话语的文字也就成了散文。”
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散文是一个疆域辽阔的文学世界,有着强大的包容力。学界普遍认为,在我国古代,最早从文体角度提到“散文”一词是在北宋时期,不过当时所指的仅仅是和驻文相对的散行文字,还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散文。大概从曹丞的《典论.论文》开始,文论家就开始正式探讨文体的分类问题,陆机的《文赋》、刘嗯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唐宋的古文家等,对散文的概念范围都有不同的理解。五四以后,散文的外延有了比较明晰的边界。倘若采用现代流行的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四分法归类,那么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比起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不但数量多、成熟早,而且内容广、影响大,绵延时间也很长。正是无数曼妙的散文作品,编织出中国历史上万类纷呈的大千世界,反映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刻画出绚丽多姿的自然风貌,描绘出喜怒哀乐的人生百态和深刻微妙的精神境界。有许多经典作品,成为伟大的中华文明的载体,历经数千年的洗礼,至今仍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辉。鲁迅对此有中肯的评价:“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福建素有“散文之乡”的美誉,先后涌现出郭风、何为、南帆等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大家。生活在厦门这座海滨秀美城市的作家们,得风气之先,勤奋笔耕,创作出大量优秀散文作品。就本卷选入的80余篇散文作品而言,近十年来厦门作家的散文创作成果蔚为大观。从舒婷、李泉佃、谢泳、丹娅、朱水涌、沈世豪、曾纪鑫等创作的一批怀人之作我们可以看到,一股新兴的散文风气正在改变着厦门散文创作的格局。《灯光转暗,你在何方》是舒婷怀想好友顾城夫妇的倾情之作,作者巧妙地用不同时期写就的三首诗结构全篇,深情款款,令人动容,是我读到回忆顾城夫妇最有气度和力量的文章。
李泉仙的《记者如何自保并“以言报国”》一文,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某些执法者丑恶的嘴脸,告诚新闻工作者:不要等闲弄文字,糟蹋了这个“大人事业”。谢泳的《怀念道新》如作者一向的文风,文字淡然,叙述节制,却透出一股凛然的悲伤。厦门读书界有一个共识:谢水的加盟,给厦门的散文随笔写作捉供了一个新视角。丹娅的《天并》是一篇精妙的文字,作者透过天井这扇“开向天空的门”,仰头看月,俯首人生,恰是月光如水,世事难测,“可望而不可即”也。朱水涌的《“回家的感觉”》追忆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的两次厦门之行,材料扎实,叙述从容,让一位低调、随和、友善、谦逊的慈祥长者形象活灵活现在读者面前。李启字的《鲁迅缘何离开厦门大学》一文,通过对史料的细密梳理,试图揭示鲁迅当年“为什么会到厦门大学,又为什么只待了短短的134天就逮然离开”这一历史之谜。作者认为,鲁迅到厦大任教并非如鲁迅自己整理的自传所说是因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捕拿,而是为了应对与许广平的恋情引发的风波;他后来遂然离开,同样是因为他对爱情的执着与疝狂。真相也许永远被历史的尘埃遮蔽,但这种探讨是有益的。老作家沈世豪对毛泽东怀有真挚的感情,在《静静的临江楼》中,毛泽东再次成为他笔下的主人公。作者再现了毛泽东身处逆境落魄时候的复杂情感和思绪,更写出了闽西百姓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保护。小说、散文、戏剧“三栖作家”曾纪鑫在《失去语言的声音》中,运用大量的细节,把故乡残疾人“龙哑巴”介绍给读者,为厦门散文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个新形象。忆人之作,“真”字当头,最打动读者的不是人物经历的曲折,而是作家在写作中表达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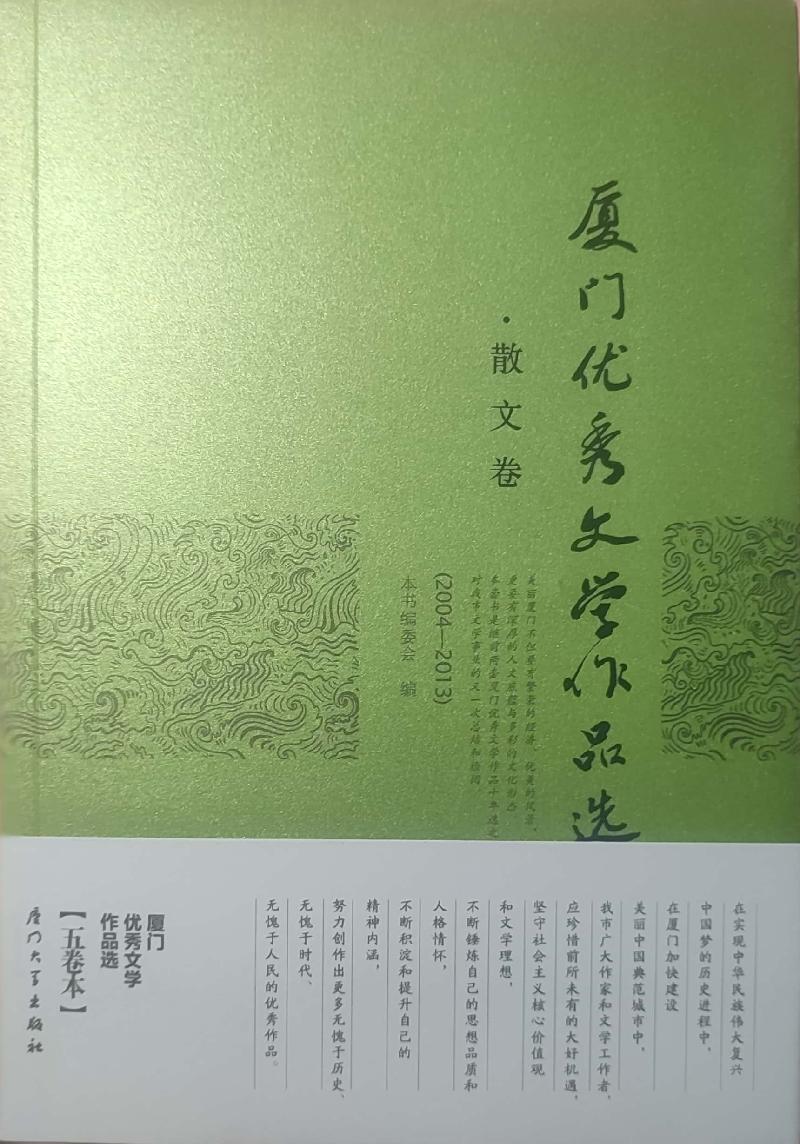 46.55
46.5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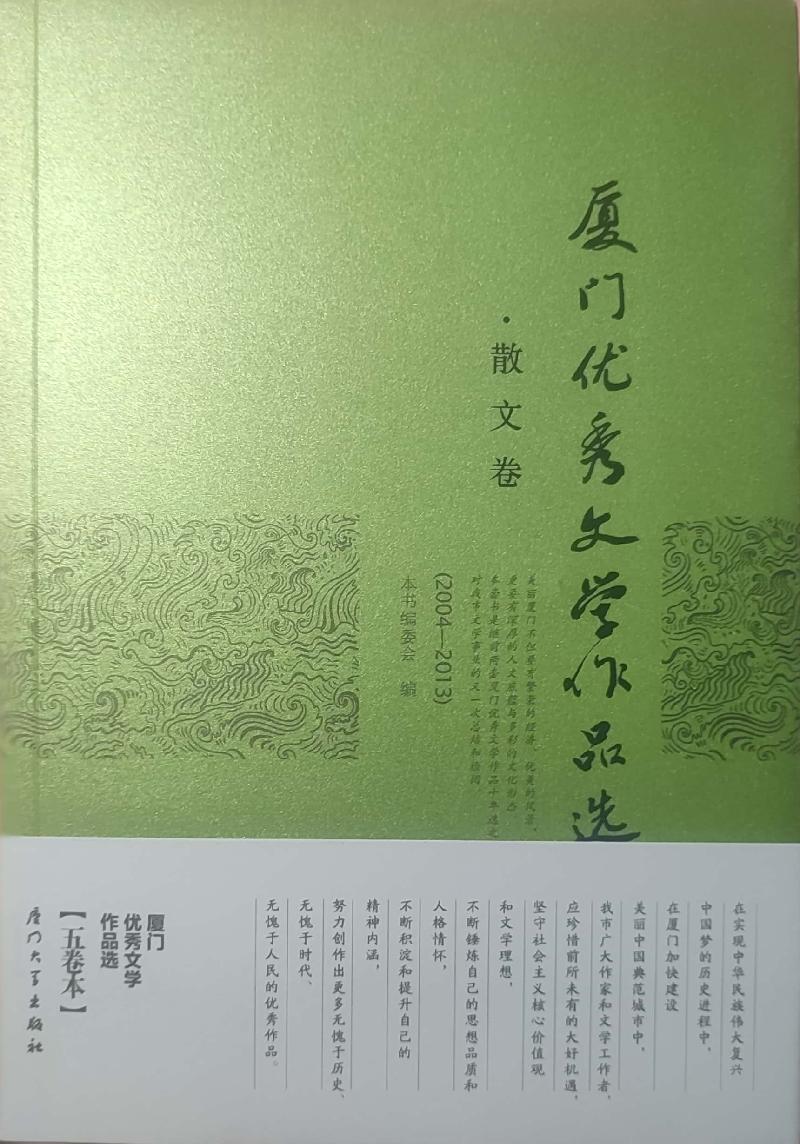
最新评论